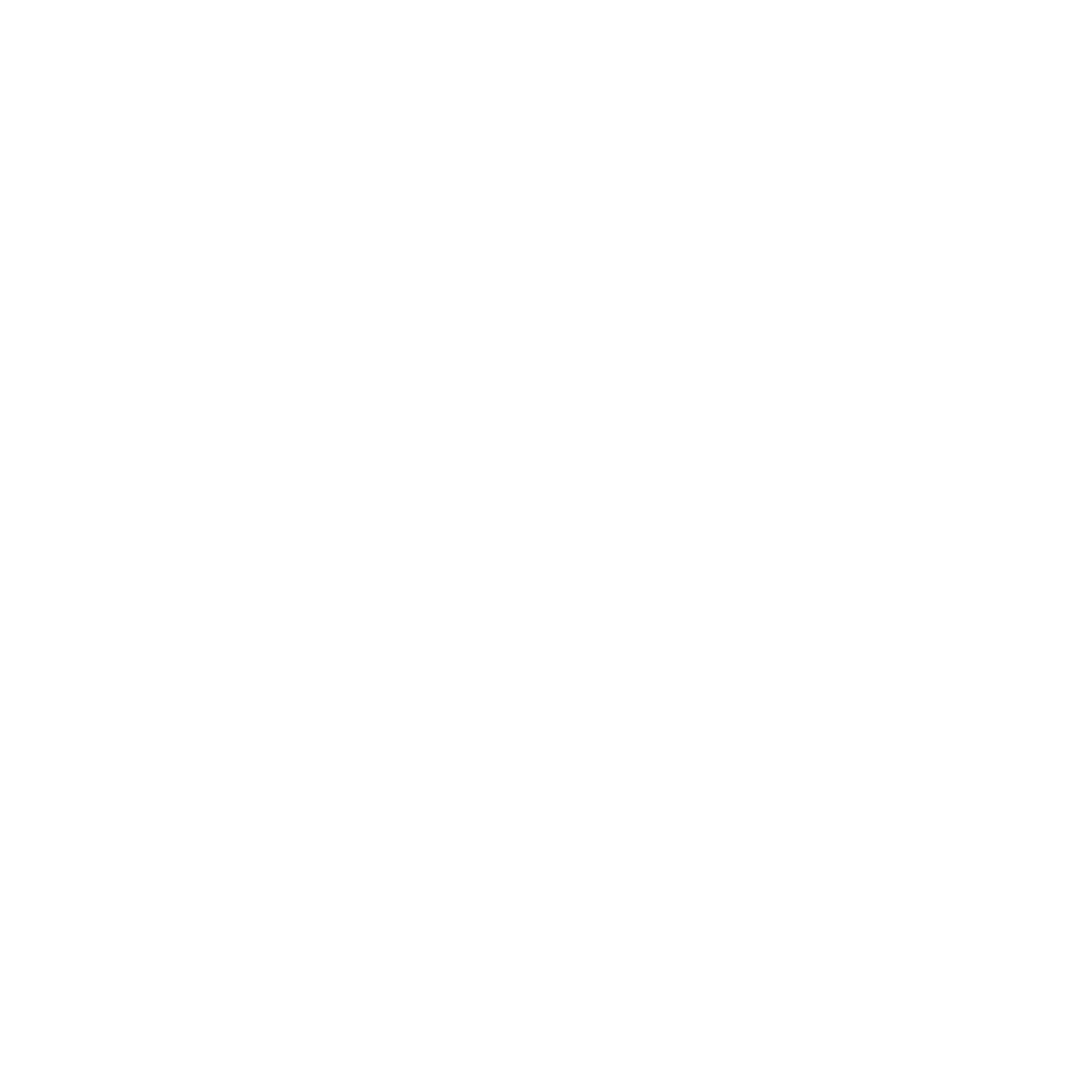父亲与他的拖拉机【文/文子】
从我记事开始父亲便开始开拖拉机,八十年代初,父亲为农村合作社开拖拉机跑运输,九十年代开始,合作社倒闭,父亲凑钱买了拖拉机,靠拖拉机跑生意、做农活养家糊口。那时候经常听母亲说,别看这拖拉机垮的不像样子,正是因为它,才有你儿时的“小康生活”。母亲也总能从哒哒哒的拖拉机轰鸣声中分辨出父亲的车,不记得是多少个寒冬腊月的夜晚,伴随着哒哒哒的拖拉机声,母亲披着衣服为干完一天活得父亲打开大门、拉亮门前的路灯……
父亲的生意无非是在附近的村子里收购农产品,然后用拖拉机拉到乡里的农产品收购站倒卖,从中赚取差价。父亲收购产品的品种也是多种多样的,小麦成熟了贩小麦、稻子熟了贩稻子、还有花生、油菜、豆子、甚至还有各种中草药、以及废弃的铁或者铜等金属材料。每每等到秋季农村收割上岸,父亲便哒哒哒的开着拖拉机四里八乡的跑,只要拖拉机停在村子中间,乡亲们就知道是父亲来收粮食了,父亲挨家挨户的询问,还要将一包一百多斤的谷子扛到拖拉机所停放的位置,而这路途当中,又是下坡或者上坡,走一些鸡肠小道是常有的事,每次一车谷子往往有二三十包…….在父亲的车里永远有一杆秤砣重的我都拿不起来的秤,这秤的秤法也比较简单,秤下有一柄铁钩,用这铁钩勾了要卖得东西,在秤的头端有一个扣,将扁担或者什么棍棒之类的穿进这扣子里面,然后两个人一抬起,拨动秤砣就可以秤出重量了,父亲开始拨动秤砣,“111斤,除批110斤……“那时候,我正读小学,周末放假,我便经常在拖拉机的车斗里,坐着或者躺在众多的麻袋上,当父亲的小会计,父亲唱完斤数,我便在父亲的账本上记下,等到所有的粮食都秤完,我就会很快的笔算出粮食总共的重量,”一共873斤”,父亲便告诉我,每斤的价格,“算6毛一斤”,我便笔算乘法,告诉父亲一共的钱数,等到父亲和乡亲用计算器各算一遍后,每每这时乡亲都会夸奖道:“这孩子真聪明,考试考第几名……” 诸如此类的话,对于那时候小小虚荣心的我,也往往是乐此不疲。 父亲与乡亲算完账,总要攀谈一会,父亲递上一支烟,也给自己点燃一支,“今年的收成不错呢,”父亲会心的说。 “ 10斗(2斗为一亩)田的谷子,除去给上面交的’公粮税费三提五统’,就这卖的了,今年的谷子又这么便宜,买不了几个钱,家里2个伢读书,每季的学费一个400多块…..你家伢上几年级了......” 乡亲边摇头,边巴拉巴拉的抽着烟说。那时候,跟着父亲,听得最多的就是”公粮税费三提五统“这些,年少的我,根本不知道这些所代表的含义,但是我无法忘记,父亲与乡亲们攀谈时,提到“公粮税费三提五统”时脸上复杂的表情。秤完谷子、算完账,父亲又要将这一包一百多斤的谷子搬上拖拉机,堆放牢实了,防止在颠簸中掉下来。
那些年父亲做生意跑过很多的村子,我也跟着父亲去过很多的村子,其中有十几户甚至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也有几百户的大村庄,而在每个村庄几乎都有熟识的人,做不成生意的也不免经常会攀谈几句,“庄家收成如何……今年的谷子什么价格……谁家的媳妇生第三胎,为了躲避计划生育跑到外地,家里房子被强拆……谁谁家超生罚款......家里娃上初中了,现在一个季度学费600多块是整年的收成……” 我坐在父亲的拖拉机车斗里,被清晨乡村的露水洗礼过、被正午的艳阳晒得黑黝黝、看过无数乡村人家的袅袅炊烟、看到过被拆掉的房子半瓦不存……等拖拉机的车斗堆放得像座小山时,父亲又驾着拖拉机提心吊胆的颠簸在去粮站的黄泥土路上,随时提防着“农机”、“税务”、“工商”、“养路费”相关部门的相关人员,来拦车征税。每当乡亲打趣父亲好生意时,父亲总是摇摇头。殊不知,这“四座大山”也让父亲承受着太多的辛酸和无奈。这种强征设卡的做法,还经常伸展到乡村小道和任何拖拉机能跑的道路,而一旦被拦截,就是扣车扣人,无论是何时何地,那怕刮起了风、下起了雨,不交钱?想走?没门!而仅“农机”部门的税费一年就是800多,要知道父亲往往要跑近一个月的生意才能赚到的,父亲经常被拦下,竟也经常分不清到底是那个部门在征税。我坐在车斗里,经常听到他们跟父亲讨价还价的。如果遇到父亲身上带的钱不够,那就只能父亲开着车到粮站交完粮之后,付了他们钱,缴了税,才肯罢休。倘若遇到粮站没现钱收货,父亲和拖拉机是不让走的,只能是我在夜色中抄小道奔跑着回家,等母亲走家串户的凑了钱,我才在二堂伯的陪同下,在黑漆漆的夜色中,又抄山路去赎“父亲和拖拉机”。
尽管如此,父亲也不是总有生意做的,农忙的时节,又要做农活。我的家乡属于丘陵地带,农业生产不适合机械化的大规模耕作,山地丘陵比较多,水稻田最大单位面积也不过2斗(1亩),所以,所有的生产活动,都要靠人力来完成,家家户户老老少少耕种的季节,都得弓着腰在稻田里插秧,秋收的季节,又得弓着腰在稻田里挥着镰刀收割,无论是耕种还是收割,每到这个时候的农村,简直是热火朝天了,大人唤小孩的声音、乡亲们隔着几亩田对话的声音,河南小贩收辫子的吆喝声…….也许大概是村子里面的鸡狗听不懂这乡外的语言, 惹得一声狗吠,这一声狗吠又引得全村鸡鸣狗叫,可谓一犬吠形,百犬吠声。 担货郎卖冰棍西瓜的叫卖声,又引来小孩们的围观,田间地头又传来父母教训孩子的声音和小孩没被满足要求的哭闹声,真是好不热闹。 每到秋收的季节,家家户户像是在竞赛,在稻田里飞快的挥动着镰刀,而父亲在田间的镰刀挥动得更快了,父亲知道等收完稻谷,就得碾稻谷了,而村子里就父亲的一辆拖拉机,都得靠拖拉机来碾,自然到时家里就少了父亲这个劳动力了,更重的收割担子将会压在母亲身上。村子里有两个稻场,而村子里几十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想趁着天气好,赶紧碾了谷子,一旦下雨,堆放在一堆的草垛因为没有完全晒干,会导致谷子发霉,所以乡亲们都得协商着碾谷子的事情。所谓的碾谷子,就是父亲卸了拖拉机的车斗,车头拉个大石磙,父亲驾着车在已经铺好的谷堆里做圆周运动,等第一轮碾完,父亲便开着车到另一个稻场,而这个稻场的乡亲便开始翻动谷堆,准备着父亲来碾第二轮,父亲没有手表,也从来不计拖拉机研了多少圈,谷堆上的谷子碾下的程度,全凭父亲多年经验。附近的村子没有拖拉机或者本村拖拉机不得空的,父亲也得兼顾着。每到这个时候,哒哒哒的拖拉机声音,总会不停的响上几乎一整天,而作为司机的父亲,还要经常帮助乡亲翻谷堆,所以一天下来根本没有空闲的时候。父亲房间的抽屉里,总放着一本绿色软皮的账本,翻开一页来看,上面歪歪倒倒的记录着,“XXX家八月初二打谷二场……”然后,再翻几页,中间又夹着几张欠条或者收条之类的,再往后翻,又有被撕掉一半的,然后还有刚写了几个字,又划掉的……母亲总是嗔怪到“真是一本狗肉账,哪个晓得记的什么”,然而,父亲在年末拿账本与乡亲结账时却从来没有算错过。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丽粒粒皆辛苦”,这首古诗,使自小帮家里干农活的我,有非常真切的感受,也使我走上社会后,成为之所以特别厌恶浪费粮食的人和事的原因。每一粒粮食都凝集了一滴汗水,尤其对于完全靠人工耕作的家乡人有非常特别的情愫,所以小时候只要是剩下饭,都免不了一顿训斥甚至一顿打骂。这些粮食,不仅是乡亲们一年的口粮,还有一部分交给上面,被称作”公粮税费三提五统“,结余的可以变卖作孩子的学杂费和学费。等到收割上岸,父亲载着半车的粮食,又颠簸在泥泞的黄土路上,前往乡里的粮站交公粮,带着袖章穿着工作制服的工作人员大模大样的拿了像柄剑似的铁器挨个的插进每一包谷子里面,然后,抽出来,将谷子倒在手上,捻起一粒像嗑瓜子一般,似乎在品尝着谷子的味道,如果检查完,没有发现发霉或者没有掺沙子和泥土之类的,就过磅秤,做记录,这一年的公粮就算交完了。我清楚的记得,有一次由于农活比较忙,大约挨到黄昏的时候,我才跟父亲去交粮,到了粮站,工作人员一句,“今日不收粮” 便将我和父亲拒之在大铁门之外。父亲只好拖着半车的谷子返回,但是在半路上,天公不作美,拖拉机的轴承坏了,天色已经大暗下来,我蹲在路边,拿着手电筒凭着手电筒昏暗的光帮父亲装轴承。装完轴承,已经是深夜了,父亲驾着拖拉机颠簸着回家,那晚在家门口的那条路上,没有看到母亲张望的身影,而家里依旧灯火通明,待父亲停下车,我们从车上跳下来,饥肠辘辘的走进家门,看到母亲在堂屋嘤嘤的哭泣,厨房里也是冷冷清清,家里坐着邻居和村里人,后来才得知,计划生育的缘故,因为弟弟和妹妹都超生,计生办扬言要十五天之内交罚款20000,不然就要抓人、拆房子。家里的气氛变得非常压抑,村里人都帮着出谋划策,诸如找关系疏通此类的办法,不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只是模糊中记得父亲,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烟,我分明看见他那被烟熏得发黄的手指开始有些颤抖…….再后来,乡里人开始走出农村,到广东、到上海、到北京……也不再需要村里大队开介绍信之类的证明文件,而“盲流”这个词也被存封在历史大潮之中。
而今,父亲已愈花甲之年,拖拉机已经在好几年前就不开了,父亲结束了他近30年的司机生活,我从来没有问过,父亲也从来没有主动提过,不做司机多年的感受,恐怕这感受也是万分复杂的。前段时间回了趟农村老家,我在大路上下车,背着行李特意走了那条父亲开拖拉机走过无数次的乡间小道,多年不走车,恐怕也很少走人的小道,草木已经长得可以伸到我的腰间,有几段路已经被雨水冲破而残破不堪。正是仲夏,树上的禅肆无忌惮的鸣叫,路边草木灌里还不时跳出来一只土蛤蟆,青草的汁液将我的白色球鞋染成了青色,我踏上村里五六十年代建设的水电站的坝堤,在这多雨的季节,小河却干涸了,河道收窄,河床长满的水草,往日坝堤下潺潺的流水只是叮咚作响,小河两岸的稻田也大多荒芜,河岸上的稻场也是杂草丛生,垃圾成堆……我远远的就看见了守望在门前的父亲,他步伐依旧矫健的向我走来,只是一路咳嗽不停,父亲边走边大声的跟村里人打招呼,待他走到我跟前,更是咳嗽的厉害,我知道这是他抽烟多年积起的气管炎,他非要将我的行李接过去,抗在肩头,又“问我几点下得飞机?一路坐了多长时间的车……”, 父亲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当父亲背着行李走上门前的小土坡时,我看见父亲已经开始有些吃力了,他的步伐开始慢了下来,喘气声变得更大,时而伴随着几声剧烈的咳嗽,他的腰弓的更弯了,刻意染黑的头发也掩盖不了他早已斑白的两鬓,父亲身穿的已经穿了几年的汗衫此刻变的十分宽松,强健的手臂没有了那曾经强壮的肌肉,一双手的手背已经是青筋崩出……我强行将行李接过来,扛在肩头,行李不是很重,然而似乎像是父亲扛过的百斤的谷子。路上遇到本家的堂伯,我问父亲堂伯六十几了,“再过几年就七十了”父亲回答我。我说“他们不种庄稼了吧”,父亲说“还种些,种些口粮,顾自己吃的,田基本没人种了,大半都已经荒芜”。 我正想问些别的,父亲又一阵咳嗽,“他们老两口现在每个月每人可以领取70块钱的……” 父亲支吾着说。我听到父亲这声音里竟夹杂着许多的欣喜。我知道,父亲想说的是:“他们老两口现在每人每月可以领取70块钱的社保”。“社保”这个对于父亲还很新的名词,我不知道该怎样更好的解,因此我竟也无言以对。
父亲真的老了,而我也不再是那个躺在父亲车斗里的青涩少年,多年来,为了寻找自己心中的答案,为了摆脱那份所谓的小农意识的束缚,来遥远的北方求学,又往遥远的闽南谋生,看过江南的小桥流水、漠北的孤烟落日,踏遍了三山五岳、越过了长江黄河……纵使万水千山都走遍,当我踏上乡间的小道,穿过杂草丛生的稻场,总能感受到这里曾经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当我用力感受着自己的黄金时代的同时,而这里不正是父亲的黄金时代吗?夕阳西下,黄昏静美,父亲与我一前一后的走着,余晖将我和父亲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编辑/九夕】这篇文章,我放在心里来来回回读了好多遍,我仿佛看到一个高大的背影,在并不宽敞的人生路上坚强的行走,为妻子儿女撑起了一片天空。语言很朴素,却很温暖,以父亲的拖拉机为主线逐渐在读者脑海中描绘出父亲年轻时候勤恳卖力顾家的形象,也同时影射八十年代初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人民生活艰辛,法律并未完善等等社会现象。儿时每个记忆细节都在作者的脑海里来回重演,好像每每想起依旧会听见父亲的拖拉机“哒哒哒”的声音在耳畔回响……现在作者已经长大,离开了父亲的庇护,走遍了江南西北,发现,父亲老了,吃力的走路,欠佳的身体,变弯的脊梁,甚至连70元的社保都会觉得开心的父亲真的老了……我想起一句古话“父母在,不远游”也许正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作者对父亲的爱和敬意随着父母亲的渐渐衰老而愈发强烈!文章思路清晰,表达明确,线条清楚,不失为一篇佳作!感谢作者惠稿凤舞九天,遥祝秋安!再次期待佳作!
【编辑/九夕】这篇文章,我放在心里来来回回读了好多遍,我仿佛看到一个高大的背影,在并不宽敞的人生路上坚强的行走,为妻子儿女撑起了一片天空。语言很朴素,却很温暖,以父亲的拖拉机为主线逐渐在读者脑海中描绘出父亲年轻时候勤恳卖力顾家的形象,也同时影射八十年代初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人民生活艰辛,法律并未完善等等社会现象。儿时每个记忆细节都在作者的脑海里来回重演,好像每每想起依旧会听见父亲的拖拉机“哒哒哒”的声音在耳畔回响……现在作者已经长大,离开了父亲的庇护,走遍了江南西北,发现,父亲老了,吃力的走路,欠佳的身体,变弯的脊梁,甚至连70元的社保都会觉得开心的父亲真的老了……我想起一句古话“父母在,不远游”也许正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作者对父亲的爱和敬意随着父母亲的渐渐衰老而愈发强烈!文章思路清晰,表达明确,线条清楚,不失为一篇佳作!感谢作者惠稿凤舞九天,遥祝秋安!再次期待佳作!
|
|